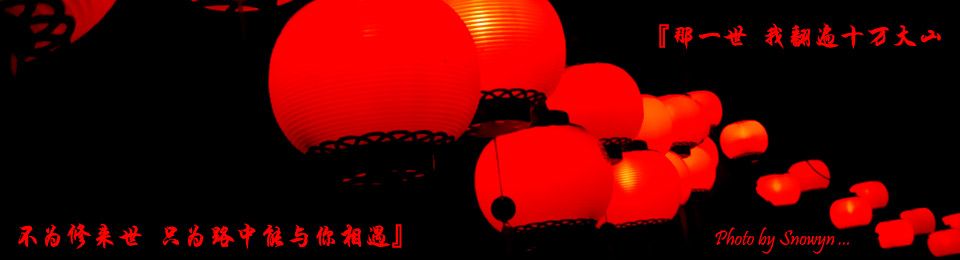一想到这搜船上可能有感染者或者投毒者,我的神经不禁开始紧绷,倘若是这样,那董小姐闭门不出的行为,便显得十分合理。她当初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我们的挖掘营地,帮我们驱散蛇群的行为,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让我一度以为她是一个神秘的巫师,有着某些超越常人的本领。
可是如此一位异能之人,不应该是恐怖的制造者吗,怎么还会害怕瘟疫病毒,或者那些投毒之人;这是否暗示了那些投毒之人的本领更加骇人。
其实我最开始怀疑董小姐的话,并不是因为有人要暗杀她,而是她说的这所谓的投毒之人,到底是否存在。虽然瘟疫这种东西已经有了几千前的历史,但是对于瘟疫病毒的发现,不过是上个世纪末的事情。之前的人类对于病毒的认知非常匮乏,瘟疫曾一度被解读成魔鬼的诅咒。如果不是微生物学或者医学领域的专家,是很难得知病毒的结构与传播机制这种专业知识的。对于病毒的科研经费,可是一笔不小的财政开支。在我们美国,目前都没有几家研究机构愿意在此投资,更不要说董小姐目前所处的羸弱的国家了。她的国家目前正处在时局动荡时期,多数的资金应该投入在军工或者农业这些立竿见影的方向,怎么会有多余的资金搞病毒研究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。如果连原理和制造都没搞清楚,那么更不要说应用与配送了,这又不是炸弹,可以随身携带,说投就投。
虽然我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,但是对于病毒的传播方式,我还是略有耳闻。倘若这搜船上真有病毒携带者,那我可要提醒我们的人加倍小心,万一有人中毒,那不但会减少我们的战斗力,而且会大大增加我的工作负担,我可不想被那该死的病毒传染。报纸上报道的症状还不够骇人吗,一旦感染,我能不能挺过去暂且不好说,即便是真的挺了过去,那后遗症会怎样,都没有石锤的统计,鬼知道这是不是上帝用来标记殉葬者的方法。
我现在要不要再次投递信件,通知董小姐这船上的八起凶案呢,到不是担心被看守的同僚嘲笑;由松猜失踪,引起的这一系列案件,明显已经不是巧合了。一个顶替寡头张瑞朴上船的张先生查案跳海在先,我要调查的关键水手证人失踪在后,这一系列事情的发生,似乎都把矛头指向了这艘南安号客轮。而董小姐又是这艘船的少东家,那么这些事情是否都是针对她的呢。
诶,我为什么要担心这些呢,在强森把张先生赶下船之后,董小姐交给我的任务其实已经就完成了,我为什么要在意这些与我无关的事情呢。虽然我们火枪队每个人都对董小姐的安危负责,可是最应该担心的不应该是华尔纳吗,毕竟他才是那个最想与董小姐谈生意的人。而我只是一个医生,又不是警署的人,为什么现在开始查起案了呢,我这是怎么了。我不禁苦笑,怎么一遇到跟这个女子有关的事情,我就失去了一贯的淡薄与冷静,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。
我拍了拍强森的肩膀,请他去餐厅里喝一杯,以表达对他陪同调查的感谢。我还是应该做回自己的本职工作,不应该操心与我无关的生意。这些大人物之间的瓜葛,不应该引起我的兴趣。也许我更应该关心一下病毒这种东西的种类与传播,毕竟这是与我的专业相关的课题,倘若董小姐说的那些事情是真的,那么这个东西,兴许会成为比枪炮更加有趣的武器。
傍晚,我躺在盛满热水的浴缸里,闭目养神,同时也回想着这些天发生的事情。失踪的船员和那些凶案似乎都发生在二等舱以下,头等舱看上去一切正常,倘若这搜船上真有董小姐所说的投毒之人或者刺客,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都在二等舱以下的区域活动。所以只要我们严密把守,董小姐又不出门,那么她就暂时安全。正想着,我忽然听到阳台的门有被拉动的声音。这可是6-7层楼高的头等舱,有人来拜访会走窗户进来吗。就在我拿起身边的手枪准备防御之时,只见一个白花花的人影瞬间向我砸来,同时一只手摸上我的脖子,让我瞬间失去了意识。